##绿绒上的心跳 ##
台球厅的灯光总是这样——不够亮,却足够让每一颗球都泛着象牙般的光泽。我靠在吧台边,看着你俯身击球。那件深蓝色的马甲妥帖地裹着你的身形,白衬衫的袖口挽到小臂,露出一截干净的腕线。你教那个新手如何架杆,手指轻轻压住他的指节,声音低低的,像球杆擦过巧克粉的声响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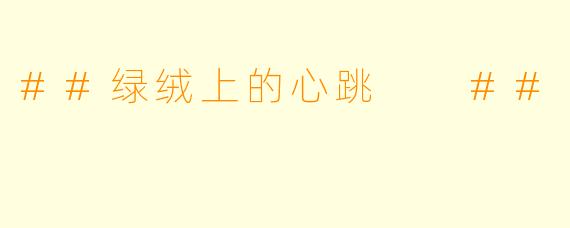
“手腕要松,像这样。”你说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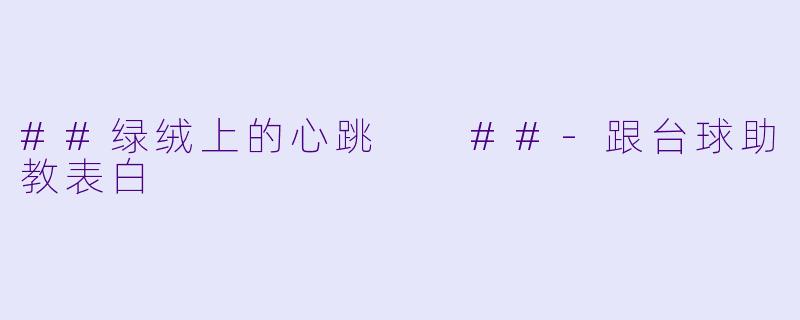
我忽然想起三个月前,第一次见你的样子。那时我刚学会握杆,母球总也打不中想要的位置。你走过来,没有碰我的手,只是把一杯水放在台边。“看球,别看杆。”你说。然后你示范了一次,那颗淡黄色的球笔直地撞向库边,又听话地滚回原点。我看呆了,你却已经转身去收拾另一张桌子。
后来我常来。周三的下午人最少,你会多教我一会儿。你告诉我什么是塞,什么是跳球,什么时候该轻推,什么时候要发力。你的话不多,但每一句都准得像你击出的球。有时候我会故意打得很糟,只为了听你说那句“再来”。你的手指偶尔会掠过我的手背,调整我的姿势。那一刻,台球厅的嘈杂——球的撞击声、人们的笑声、老空调的嗡鸣——都退得很远,只剩下你袖口淡淡的洗衣粉味道,和我自己太响的心跳。
我知道你只是助教。你的工作就是让每个客人都觉得自己能成为下一个丁俊晖。你对我笑,也对所有人笑。你记得我不加冰的柠檬水,也记得王老板要龙井,李阿姨要菊花茶。可是那天,当我终于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袋,你轻轻拍了拍我的肩,说“漂亮”时,我分明看见你眼里的光,不是职业性的赞许,而是真实的、细碎的喜悦。
此刻,你结束了教学,朝我走来。吧台的灯光在你睫毛下投出小小的阴影。你拿起毛巾擦手,动作慢条斯理。
“今天怎么不打球?”你问。
我握紧了手里的水杯,杯壁沁出冰凉的水珠。那些练习过无数次的话——关于你的眼睛像最深的袋口,我一头栽进去就再没出来;关于你教我的不只是台球,还有某种安静的勇气——全都堵在喉咙里。最后,我只是看着你马甲上那颗快要脱线的扣子,说:
“我在想一件事。”
“嗯?”
“如果……如果我请你喝一杯,不是在这里。”我的手指在杯沿画着圈,“是在没有球桌的地方。你会答应吗?”
你擦手的动作停了。毛巾搭在你掌心,像一面小小的白旗。远处,一颗黑八落袋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有人欢呼,有人叹气。而在这方寸之间,时间突然变得很慢,慢得像一颗球在绿绒上缓缓滚动,朝着未知的袋口,义无反顾。
你抬起眼睛看我。那眼神不再是助教看顾客的眼神,而是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。你嘴角弯起一个很小的弧度,不是职业的微笑,是别的什么。
“你终于问了。”你说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,“我以为你会一直等到学会清台。”
我手中的杯子晃了一下,水波荡漾,映着天花板上星星点点的光。原来你都知道。原来那些周三的下午,那些“偶然”的触碰,那些多余的指导,都不是我一个人的想象。这就像一场漫长的对局,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走位,终于在这一刻,把母球停在了最合适的位置。
你放下毛巾,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,在吧台的深色木面上画了一条短短的直线。
“这是球杆。”你说,然后又在旁边点了一个点,“这是母球。”你的指尖移向远处,“而目标球……”你顿了顿,没有画下去,只是看着我,“有时候不需要太复杂的杆法。直球就好。”
我忽然明白了。表白不需要华丽的塞,不需要炫技的跳球。就像最简单的直球,只要方向对,力道够,就能听见那一声清脆的撞击——那是心落入心袋的声音,干净利落,回响悠长。
“所以,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居然很稳,“周五晚上?七点?”
你拿起粉笔,在那条“球杆”旁写下了一个时间。字迹清瘦,就像你俯身击球时的背影。
“带好你的杆法。”你说,眼里有笑意,“不过这次,不打台球。”
我笑了。吧台那幅巨大的装饰画里,翠西·查普兰正俯身瞄准,她的世界只有球、杆和
![[助教]Logo](https://www.bdazi.cn/logo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