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绿绒桌上的童年导师:我在台球俱乐部当助教的日子》
十二岁的夏天,我的身高刚够到台球桌边缘,却意外成了社区台球俱乐部的“编外助教”。起因是总蹲在角落写作业的我,某天替老板捡球时,顺手用三角框摆了个标准开局——这个动作让我收获了人生第一份“工作”:每周六下午,帮新手孩子们调整握杆姿势,或者踮脚替他们够滚进球袋的巧克粉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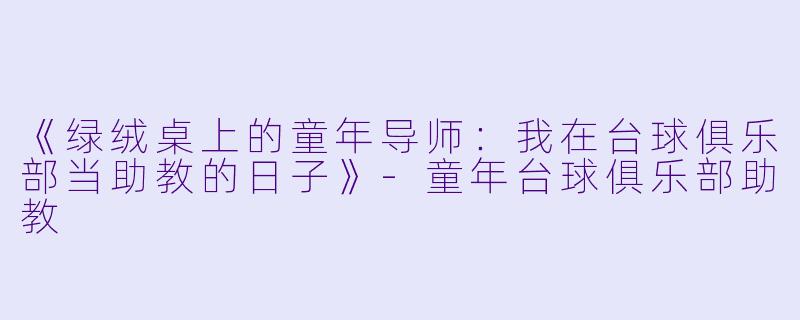
俱乐部里,台球是大人世界的社交货币,却是孩子们的巨型积木。我教六岁的豆豆用杆头轻推白球,他更热衷于把彩色球堆成“火山”;初中生小凯总想学电视里的“跳球”,结果杆头戳裂了三块巧粉。老板老张从不阻拦,只在吧台后笑:“让他们玩,台球桌比手机好玩多了。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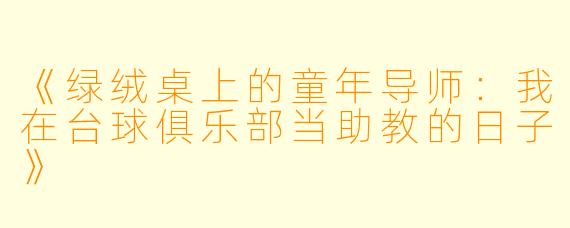
最难忘的是教患有自闭症的童童。她拒绝触碰任何人,却愿意让我握着她的手背练习出杆。三个月后,当她第一次把红球打进中袋时,整个俱乐部的大人都在鼓掌——那声音比十五局连胜的喝彩更响亮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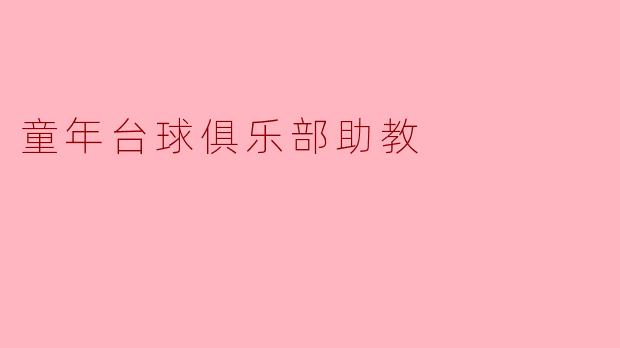
现在想来,所谓“助教”不过是陪着一群孩子,在墨绿色绒布上探索角度与力道的童话。那些被阳光晒暖的午后,台球碰撞的脆响里,藏着我最早明白的道理:教育有时不需要讲台,只需要一张能让人俯身平视的球桌。
![[助教]Logo](https://www.bdazi.cn/logo.png)